迟到十年的相遇 | 即使站在人群中,仍是无尽孤独
“我没病!我死都不去!”十年前的我也许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十年后的自己会主动踏入心理咨询室。

高三那年,因压力过大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因素,我变得沉默寡言,不与任何人交流,也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,以至到最后不想上学,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内闷头大睡。父母为此焦头烂额,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想带我去看看,但我不愿意去,甚至因此而变得更加不可理喻、暴躁易怒。
那时的我认为,心理咨询师与医生无异,医生治疗生理,心理咨询师治疗心理,我如果去了,那就是承认自己有病。除此之外的,还有对一切的抱怨与无力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,就是单纯不想动而已。
后来临近高考,我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,生活似乎开始回到原来的轨道,父母也放心了下来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的心空出了很大一块,像无边的荒原,寸草不生。

我以为生活会就这样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,直到我出来工作,那种空落孤寂的感觉逐渐像熔岩一样侵蚀我,即使我站在人群中心。就像曾经不想去上学一样,我对工作失去了所有热情,每天与同事以及亲友交流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负累,我就像溺水中抓住稻草的人,以生存为由死死维持着一丝清醒。我好像没办法再欺骗自己,我想,有病就有病吧,反正我现在独立了,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我病了。
再三抉择后,我选择开始心理咨询。不是没想过要去医院,但对医院,我总怀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抵触,选择心理咨询于我而言已是最大的勇气。
初次咨询那天我犹豫了很久,想着要不还是算了吧,也许再缓一段时间,就会像过去那样自行恢复的。况且就算我去了,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也不会理解我,她大概只会像我所熟悉的所有人一样,对我赋予或恨铁不成钢或怜悯的眼神,但无法给我任何实际性的帮助。所以,我迟到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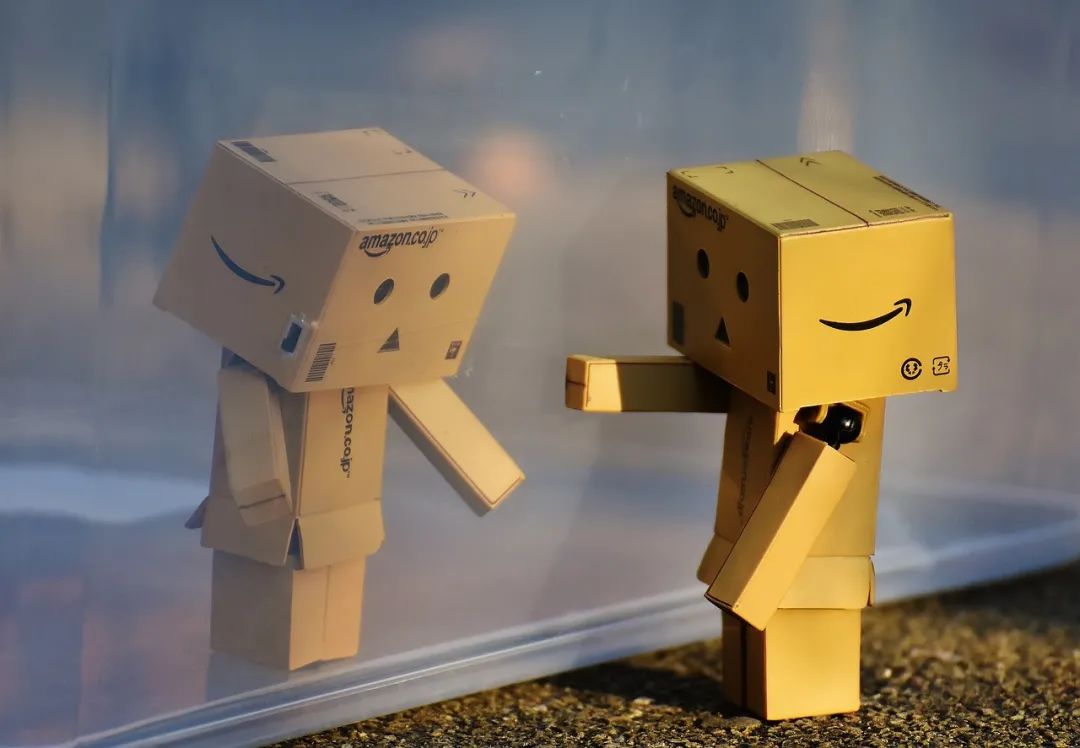
我的咨询师是一位目光柔和气质温暖的女性,我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坐下来,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,也似乎并没有什么要说的。”——我很直接地表达了这一点。她微笑表示理解,说那我们可以先来聊聊最近的状态,是什么让我走进这里,或者是我想和她分享的任何事情。
我来之前编排好了种种措辞,在她的目光下竟觉语塞,我不知道要怎么应对这种情景。
从小时候起,我身边的人一直都很重视沟通,尤其是我父母。他们总说有事情要沟通,心里有话要说出来,即使有些情况下我并不愿意说。“你怎么这样了呢?以前你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啊。”——这是他们在我没有马上对问题做出回应时的口头禅,也是我最害怕听到的话。
想到这里,我突然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,我说我很烦,不想要工作,也不想要跟人交往,我只想躺着,什么也不想管。我的咨询师,出乎我意料地没有问我为什么这样,也没有说我不应该这样,她只是静静地听着,但又确实能让我感觉到她有在认真听。“你是最近才有这种感觉吗?”这句话如同打开了我倾诉的阀门,我开始对她诉说高三的那段时光,这段我不愿对任何人提及的经历。
第一次咨询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,我奇妙地感觉心上沉重的一部分好像轻松了一些,但那些空虚的部分依然存在。我想,我下次一定不能迟到。

心理咨询不是药到病除的神药,那些曾经搁置的伤口,需要一个精心修补的过程,这段旅途也许漫长,但所幸并不孤单。我逐渐澄清了对心理咨询的一些误解,不再把它当成一种机械式的治疗,而是与咨询师共同成长的宝贵时光。这个过程并不只是轻松愉悦的,我所不愿诉说的那些话,原来只是被我囫囵包扎,把杂乱的绷带撕开后,是并未被妥善处理的伤口。我逐渐了解我不愿再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原因,父母喜欢追根究底,想要尽快解决问题,但很少过问我的感受与想法。
久而久之,这种相处方式逐渐被我泛化,我开始不相信别人能给予我包容与理解,亲手为自己建造牢笼。示弱也并不等于软弱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,我才发觉自己从来不甘示弱。
即使咨询,我也总是想把自己放在一个理性的位置,致力于塑造我想展示给咨询师的外在印象。直到有一次,咨询师说我在过去痛苦的经历里似乎一次也没有哭过,问我对哭有什么感受。我过去从不哭,因为总怕被别人问怎么了。回想起种种,却第一次在她面前流下了眼泪。
她把纸巾盒轻轻推到我面前,我抽噎着哭了很久,连我自己都感到讶异。哭完神清气爽,预想中的嫌弃没有出现。“你一点也不软弱,你很勇敢。”——咨询师的这句话,给予了我莫大的勇气。
那天我久违地回了趟家,父母显而易见地开心,做了一桌子菜,都是我爱吃的。我又哭了,哭得让父母措手不及,他们还是那样,一个劲地问我怎么了。我不说话,就只是哭。最后,妈妈和我抱在一起嚎啕大哭,爸爸坐在旁边递纸巾。妈妈说没事的孩子,觉得辛苦不想干了就回家吧,休息一阵子再说。我摇了摇头,第一次觉得与父母的心离得也不是那么远,长久飘荡的心缓慢下沉,有那么一个底子,会为我托着。

我的心理咨询之旅至今仍持续着,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某段时刻真的存在某种心理病症,但那似乎不重要了。我和我的咨询师一起拿起了缝补的针线,重新拾起那些破碎的过去。
总有一天,我必会有独自踏上征程的勇气,不是结束,恰逢新生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