拼命吃,又拼命吐?——暴食症背后的心理真相
在你身边,也许有这样一类人:
“我感到烦躁、空虚,身体里好像有个巨大的洞,我强烈的想吃东西,我必须要吃,我知道我又要发作了。我买了很多吃的,甜点、炸鸡、披萨、奶茶、很多的零食。我关上门一口气吃掉所有东西。那一刻我感到满足,但紧接着我觉得恶心、恐惧。天呐,我怎么又吃了这么多?我怎么毫无自控力?我太肥了,太糟糕了。于是我去厕所催吐,吐完了,又是深深的羞耻和疲惫,我厌恶自己。”

以上是一位暴食症患者所描述的一次发作。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暴食症。

当身体成为情绪的容器
心理学中,暴食症(Bulimia)是一种进食障碍,患者反复出现暴饮暴食的行为,并在之后通过催吐、过度运动或服用泻药等清除行为来避免体重增加。但这个症状远不只是“吃太多”这么简单。
暴食的冲动被体验为一种原始的感觉,在吃的过程中,不是为了品味不同的口味,而是为了满足某种更为原始的欲望,咀嚼、吞咽的动作本身和饱腹的感觉可以带来某种极大的安慰感、充实感和圆满的感觉。
暴食行为是在“吃”那些难以消化的情绪:被压抑的愤怒、失落的关系、不被满足的依恋、对亲密的渴望。而催吐,则是一种“排斥”,不仅是对食物,更是对内在冲突、羞耻、甚至对自己的一种攻击性释放。
患者可能在潜意识中感受到一种无法承受的融合:当我被靠近,我会被吞噬,会失去自我;当我想表达自我,我可能被讨厌、被遗弃。在这样的矛盾中,暴食与催吐就成为一种具体的、可控的身体仪式,在混乱中带来短暂秩序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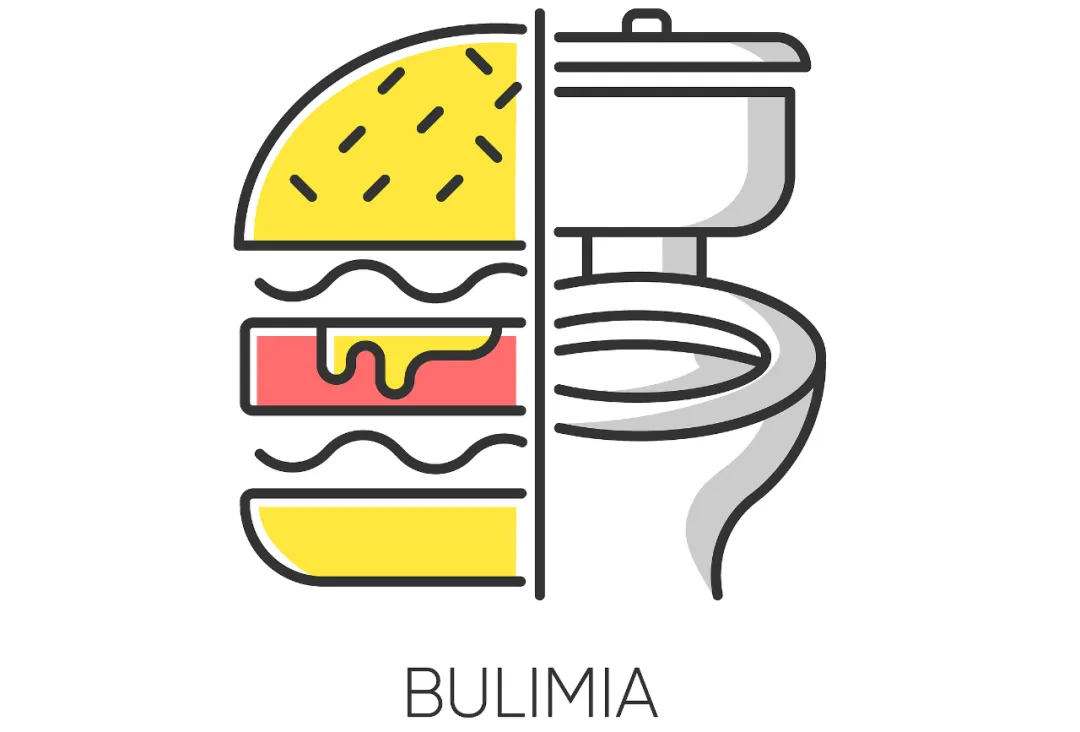
我们可以这样理解:吃,是一种融合的渴望,是希望被包容、被理解、被满足;而吐,是对融合的抗拒,是重新划清“我不是你”的边界。反复的吃与吐,是在靠近和挣脱间反复挣扎的过程。

吃进去的是爱,吐出来的是控制
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,暴食症的核心不在食物,而在关系,尤其是早期的母婴关系。
在婴儿的发展过程中,养育者不仅提供照顾的功能,也是情感调节器。婴儿通过吃来感受母亲的存在,母亲喂养的姿势、语调、眼神构成了最初的“爱”的象征。
这一阶段,“口腔”不仅是进食的器官,更是情感连接的通道。口腔的感受,就成了爱的载体。
但如果这个阶段亲子关系出现失调,比如养育者情绪不稳定、过度控制、将孩子作为自己自恋的延伸,看似给予了很多爱,但爱中夹杂了强烈的控制、期待、甚至嫉妒。那么吃就不再只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。

吃变成了与养育者合一的渴望:我吃下去的不只是食物,更是爱,吃是一种重聚的象征,我吞下这些东西,仿佛回到那个我被全然包裹、被注视和照顾的时刻。而吐,是一种挣脱:我要把你从身体里赶出去,我想证明我是独立的。
在临床中我们会听到患者这样说:“我好像不是在吃东西,我是在填补什么空洞。”这个空洞往往并不简单是情绪的,而是与“我是谁”、“我从哪来”、“我属于谁”这些深层问题有关。在最初的依恋关系中,他们没有真正感受到稳定的边界和自我,养育者既是滋养的源泉,又是压迫的源头。暴食和催吐,就是这组矛盾在身体上的具体化表达。
并且,很多暴食症患者会对自己的身体充满敌意。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,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,是某种附属品,或是“被操控的对象”。于是,暴食和催吐不仅仅是行为问题,它们成为一种对控制的反抗,对未完成心理分离的焦虑性重演。
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患者在暴食时并不真的“享受食物”,他们像在执行一项机械的仪式。他们用吃来感受到圆满,但融合之后紧随其来的,是无法承受的焦虑——觉得自己“太脏”、“太满”、“太接近那个不该靠近的人”,于是只能用吐来重新建立与自我的界限。

暴食和催吐就这样形成了一个闭环——渴望、融合、羞耻、攻击、自我惩罚,再渴望。

当身体成为“战场”:自我认同的撕裂
换个角度说,暴食症与自我认同感的模糊有关,特别是对身体的认同。
许多暴食症患者的痛苦不只是起源于婴儿期的口腔母婴关系,也关乎他们如何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建立起自体感、健康的自恋和性别身份。
暴食症患者可能从未真正拥有自己的身体。身体在他们的体验中常常是“他者期待的载体”,身体是被评价、被控制、被规训的,是母亲的、父亲的、家庭的、文化的,却不是自己的。这是一种内在认同的撕裂。
因此,他们无法在身体中感受到“我”,于是通过暴食去主导它、通过催吐去清空它。简单来说,暴食是夺回身体的激烈尝试,“我吃我想吃的”、“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”、“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”。而催吐又成了与内在冲突妥协的手段,“我太脏了”、“太自私了”、“太不应该了”。

身体成了“自我”与“非我”的混战之地。
暴食时,未被满足的渴望强行塞入身体;
催吐时,又像是要将羞耻、内疚、冲突通通清除。
著名自体心理学家 Kohut 曾指出,稳定的自体感来源于早期镜映的成功,我们被看到、被回应、被欣赏。而在许多暴食症患者的成长环境中,这种镜映被权力、控制、羞辱或忽视取代了。于是他们习惯于将自我需求藏起来,只留下一个“功能性自我”,一个面具,迎合他人的期待。
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往往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,对身体、饮食、生活方式都严格苛刻,“控制”是应对内在混乱和界限模糊的方式。可惜的是,这种控制建立在极端的否定和羞耻之上,并不带来真正的稳定,而是形成了更深的自我分裂。压抑欲望,欲望总会反弹。
此外,一些精神分析学者认为,这种“暴食—催吐”循环,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性化的幻想。食物替代了情欲对象,进食象征着融合和性过程,催吐象征着堕胎、排斥、惩罚等。听起来有些抽象,不作展开,但在精神层面,暴食确实通常也和性议题同时出现。


疗愈的开始:分离、命名与重建“我”
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并不只关注“吃得好一点、少吐一点”,而是要帮助患者慢慢建立一个可以承载自己的内在空间,将用身体演出来的冲动转化为能够说出来的能力。
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,往往需要从一段安全的、真实的关系中开始。
精神分析治疗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场所:
在这里,可以体验到“不被控制也能被理解”;
试着把过去“吃掉”的感受说出来,而不是吞进身体里;
慢慢区分哪些是我的感受,哪些是他人的期待;
在不被吞噬的情况下,开始拥有自己的想法、渴望、节奏。

治疗的目标,不是彻底消除暴食症,而是让症状不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。在治疗过程中,患者慢慢学会把“吃进去的情绪”转化为语言:可以开始表达愤怒,而不是用食物麻痹愤怒;可以谈论羞耻,而不是用催吐洗净羞耻;可以感受到渴望,而不再因为渴望而惩罚自己。
暴食症,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关系病:对早年依恋失败的哀伤、对失控自体的恐惧、对被吞没与被抛弃的双重焦虑。而疗愈的起点,是重新建立一种“我可以是我,而不是你”的自我经验。
所以,当你再看到一个人在卫生间里小声呕吐,请不要着急评判。他的身体,正在替他承受一场来不及言说的心理战争。
如果你自己也正经历这一切,你不是孤单的,你也并不软弱。暴食症不只是对食物的困惑,更是对存在的追问。它是一个人在成长中被压抑的自我,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呐喊:“看见我、理解我、让我做我。”

愿这份被看见的旅程,能够帮助每一位身处症状中的人,走出身体的牢笼,走向一个真实、自由、有边界的自我。
-THE END-




